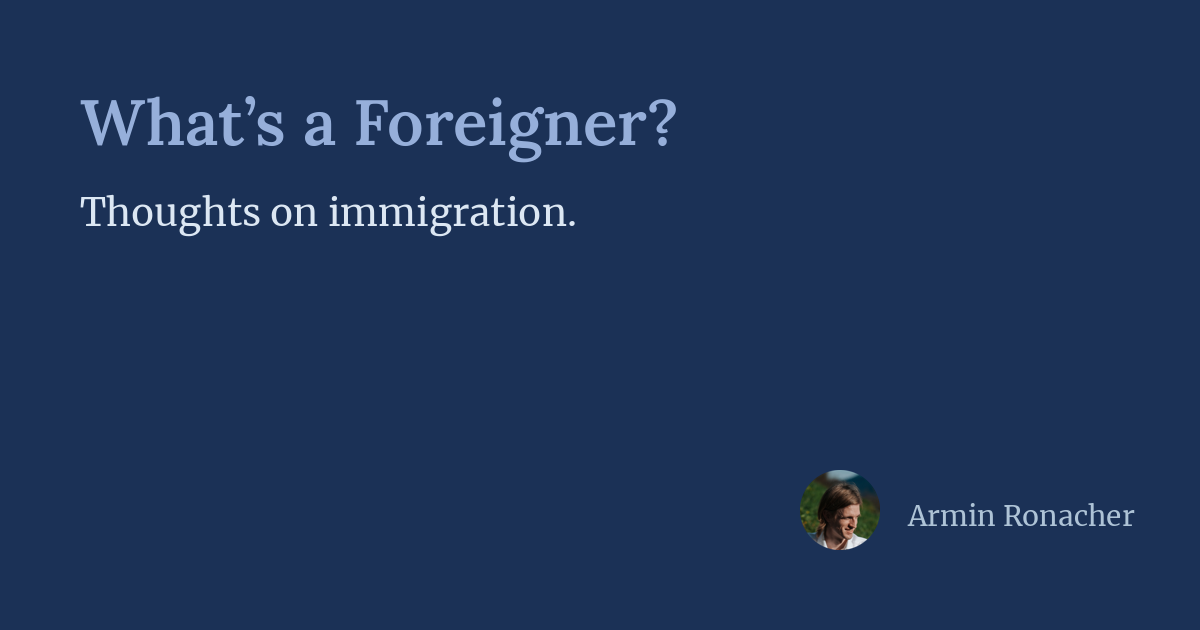
在许多国家,对移民的抵制情绪正在高涨——即使是像日本这样移民很少的国家,现在也出现了反移民集会。我不会在这里偏袒任何一方。我想探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说“外国人”时,我们指的是谁?
我认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法律各不相同,社会定义也各不相同。在我居住的维也纳,移民现象随处可见:大约一半的小学生在家不说德语。奥地利很难获得公民身份。许多出生在这里的人并不是公民;与此同时,居住在这里的欧盟公民享有与奥地利本地人类似的广泛权利和劳动力市场准入。在我的一生中,对外国人的恐惧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针对附近的东欧人,现在更多地落在欧盟以外的人身上,通常是通过宗教或文化来界定。实际上,“外国人”越来越多地意味着“非欧盟人”。请记住,在过去的 30 年里,欧盟国家从 12 个增加到 27 个。这是社会流动性的显著提高。
我认为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如今美国的争论与公民身份和效忠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美国国内的斗争包括试图缩小出生时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人们的担忧并非在于哪些外国人会来,而在于成为美国人的条件,以及新移民是否会接受一些人所定义的美国价值观。
在欧盟内部,欧盟公民身份的概念改变了社会现实。自由流动、统一的标准、互通的社会体系以及更便捷的劳动力流动,使得欧盟公民彼此之间不那么“陌生”——尽管存在着实际的摩擦。脱欧前的英国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可见的方面,英国的融入程度较低,而且对中东欧工人更具敌意。这或许是融入程度至关重要的另一个迹象。实际上,欧盟内部对效忠的界定也远不明确。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其他欧盟国家,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明确地指向任何一个国家。
合法移民本身被广泛误解。大多数移民制度在某些方面限制性极强,但实际上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宽松得多。一方面,所谓的“非法”移民往往完全合法。许多被视为“非法”的人正在合法等待庇护裁决,或者已被接纳为难民。许多人认为这些程序不应该存在,但事实上却是合法的。另一方面,非庇护移民的门槛非常高,而且大多数本国公民本身都没有资格获得技术移民签证。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可以简单地“驱逐所有外国人”的想法在实践和道德上都陷入了死胡同。人口流动压力并未消失;大学、企业、个体雇主、人口结构和地缘政治因素都在加剧这种压力。
公民身份只是个小问题。在奥地利,你通常需要通过一项简单的德语考试并放弃之前的国籍。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结果:土生土长的非公民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却没有护照,而入籍的公民却从未完全学会德语。法律上清晰,社会上却混乱——这并非奥地利独有。获得护照的高门槛也导致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故意选择不成为公民。放弃护照的代价不容小觑。
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国际流动的现实使得我们目前的移民类别捉襟见肘,与广大民众对移民的认知相去甚远。经济焦虑、战争和政治两极分化使一些外国人群体成为攻击目标,而移民背后的深层驱动因素只会不断加剧。
或许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都在纠结于这些问题。那些担心社区或国家变化过快的人,以及那些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都在应对着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在这个资本自由流动而大多数人却无法自由流动的世界里,在这个气候变化可能很快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世界里,在这个富裕国家出生率急剧下降的世界里,我们的移民制度将面临考验和压力,而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很可能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