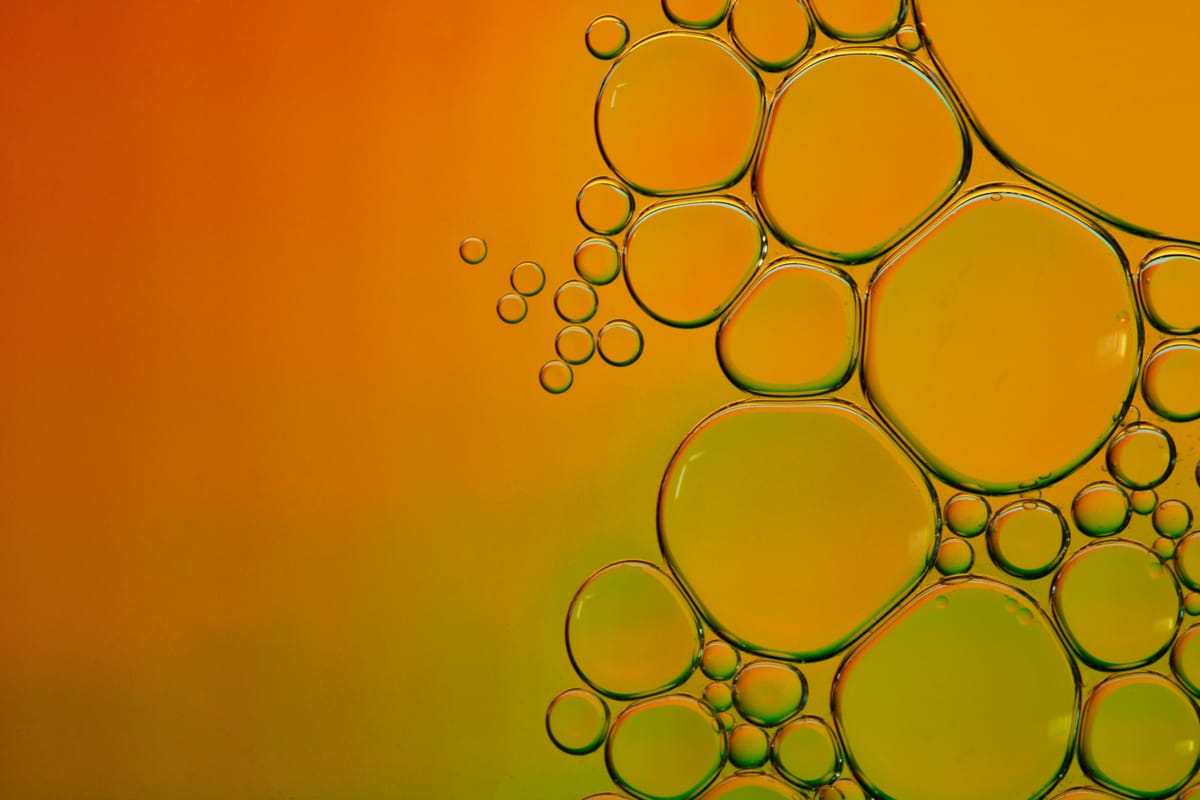
我发誓,现代美术馆开始使用 LED 灯代替白炽灯泡,这真的毁掉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壁画。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常常会抱怨,他们把年轻时那些像氦气球一样飘荡的记忆,与当下沉重的现实体验进行比较。所以,如果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要么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画作时的感觉有误,要么是画廊还在使用白炽灯泡,而我的记忆有误。
但我一生中看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N次,前N-2次是在书中看到的复制品,当时我觉得“嗯,我看不懂”,第N-1次是在白炽灯泡时代亲眼看到的,真的让我热泪盈眶,第N次是在我发誓是LED灯的灯光下亲眼看到的,(我发誓)那灯光让这幅画看起来扁平而单薄。
我们完全有能力在需要的地方继续使用白炽灯吧?或者至少找到光线特性与白炽灯相似的LED灯?
这让我不禁思考,有多少艺术作品我从未欣赏过,仅仅是因为它们创作时的光线——无论是特定时间或地点的自然光、烛光,还是艺术家作画时使用的其他光源——与我看到它们时的光线截然不同。这就好比洞穴壁画是为了在篝火的映衬下而创作的,又或者(出人意料地相似)像素画如今在我们看来略显粗糙,但它最初是为CRT显示器设计的,CRT显示器能够赋予画面自然的动态效果。
如果你从字面上用错误的方式看待一件艺术品,那么从比喻意义上讲,你也用错误的方式看待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它。 看到了。
卡斯滕·霍勒的作品开启了我对当代艺术的全新认知。 测试场地,是一系列为成人设计的滑梯,安装在一个巨大的展厅里,虽然严格来说并非无边无际,但确实非常巨大。
这正是那种经常被嘲笑为“当代艺术出了什么问题”的艺术作品,因为穿着衬衫和花哨围巾的成年人从大型游乐场滑梯上滑下来(不得不承认)非常滑稽,而这些滑梯的建造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维护费用更高,这一点也很容易被嘲笑。
但《测试场地》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滑梯本身,而在于你排到队伍末尾时的感受。在轮到你的时候,会有15秒钟的时间,你其实并不想再玩了——毕竟你是一个穿着西装的50岁男人,你突然想起自己5岁时也害怕滑梯,但邻居家的孩子(他总是比你勇敢)却在喊: “快点,下去吧!”你不得不去做,即使你不想做。20年后,你的婚姻也变成了这样。你知道你不想继续下去,但一旦你在那条隐喻的队伍里站得足够久,你就无法抽身,你知道吗?你会想邻居会怎么想。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妻子令人精疲力竭的僵局,她的无奈最终比她的愤怒更糟糕。她终于发了慈悲,把这段婚姻带到后院,一枪毙了。你的朋友们(你私下里肯定)都觉得这让你颜面尽失,但对你来说却是一种解脱,因为你永远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所有人都盯着你看,因为已经过了30秒,队伍在你身后越来越长,他们开始不耐烦了,因为你现在在卡斯滕·霍勒的测试场地,他们需要你滑下去,这样他们才能滑下去,然后告诉所有人。早午餐时,朋友们说这事儿多傻啊,但你知道吗?让他们嘟囔吧,让他们生你的气吧!你这辈子就这一次,要选择你自己。你转过身,看着他们——这些一辈子都在潜移默化地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的人——你高举双臂,向他们做出反抗和自由的姿态,(即便不是真的)这在你脑海中,就像一只折翼的鸟儿展翅高飞,然后你离开了队伍。
艺术作品《测试场地》的重点并非滑梯本身,而是排队等候体验滑梯时的感受——排队本身就是测试,而你就是场地。即便它不过是一群成年人乘坐昂贵的游乐场滑梯,它仍然是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
总的来说,当代艺术如果更多地关注它想唤起我怎样的内在体验,而不是它展现了什么,就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欣赏)。评判当代艺术的标准不应该是它展现了什么,而应该是它如何具体、独特或强烈地唤起特定的体验。很多作品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这没错!但至少我们应该根据作品的创作意图来评判它。
就像书籍(和人)一样,我认为有些艺术作品只有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刻才能被理解。我不想为所有事物辩护,我怀疑有些艺术作品(和书籍)确实很糟糕。但我会努力同时接受“这件艺术品感觉像是艺术骗局,视觉和愤怒都毫无意义”和“也许我只是没有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它,所以无法理解它”这两种想法。
就像灯光问题一样,即使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在不合适的环境中也会显得逊色。例如,我坚信罗斯科教堂与罗斯科的作品格格不入,尽管(这让我的论点显得有些尴尬)它正是罗斯科本人设计的。(他在教堂开放前就去世了,所以我只能安慰自己,如果他看到自己最终的成就,他一定会修改设计,而不是承认我错了。)
相比之下,泰特美术馆的罗斯科展厅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伟大、最深刻的人类体验之一,可以与圣家堂相提并论……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但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我再次声明,我并不是说所有东西在合适的语境下都是好的,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想说,一件作品要打动人心,需要很多互补的方面都恰到好处;如果你看到一件作品时没有产生共鸣,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件作品不好。
欣赏艺术的一大问题是,如果你花了 30 美元(或者排队一小时)去参观画廊,你会觉得物有所值,结果却在那里待了太久,看了太多艺术品,然后就不想再去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理想的观赏时间大约是 30 分钟,所以我一生中接触艺术的机会大多来自于我偶尔住在一家非常好的、非常免费的画廊附近,我可以随时进去参观。
我怀疑我们世界的艺术分布非常不合理?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无人展出,大量的优秀艺术作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而还有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优秀的艺术作品。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切实可行的个人应对方法,我想或许可以先去美术馆待半小时,然后在咖啡馆里用笔记本电脑坐几个小时,再出去待半小时,如此循环。但我从来没这么做过。
我的朋友S认为应该建一个画廊,专门展出历史上一些最伟大艺术作品的精确复制品。我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可以把它办成一个当代艺术展,探讨复制品与原作的真伪之争。
我原本想把这篇文章命名为“关于现代艺术的 X 个思考”,但从技术上讲,现代艺术指的是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现代”这个词有一天竟然会用来指代一段遥远的过去。我们或许已经跨越了那个门槛,年轻人会觉得“现代”这个词过时了,就像纽约一点也不新,新学院更是如此。如果你想让某件事物长久存在,或许用它的“当下性”来命名它本身就是个错误。
我敢肯定,在我小时候,肯定有人会说“其实这不算现代艺术,因为它是1980年创作的”,但我估计大多数人也觉得这种说法很烦人。不过,现代艺术时代结束至今已经50年了,我想是时候向前看了吧?我们都像自由自在的小鸟一样,最终都会滑落到漫长的滑梯上。
原文: https://www.atvbt.com/three-thoughts-on-contemporary-art/